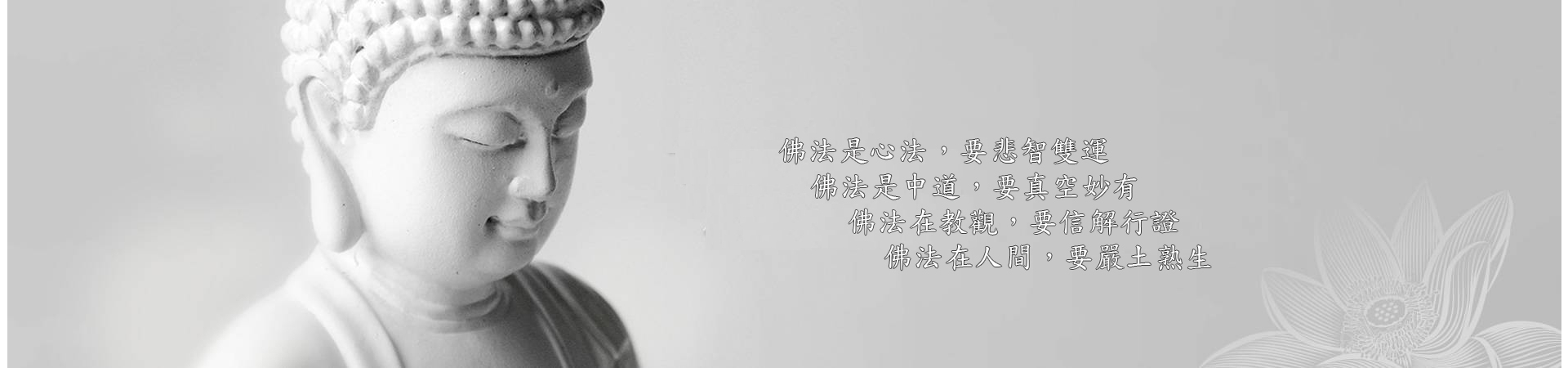《禪關策進》講記
第四講
鄭振煌教授主講
蒙山異禪師的開示,講到有一些長老教他以海印三昧ㄧ印印定,也就是永遠保持在海印三昧的狀態中,用海印三昧來反映一切的萬事萬物,其他都不管,他就聽了這句話,「過了二載,景定五年六月,在四川重慶府患痢,晝夜百次,危劇瀕死,全不得力;」在四川拉肚子,晝夜有一百次,非常危險,所有的都用不上力。
「海印三昧也用不得;從前解會的也用不得;有口說不得,有身動不得,有死而已;業緣境界俱時現前,怕怖慞惶,眾苦交逼。」這個病的相當嚴重,所有的法門都用不上力,有口說不得,講不出話來,身也動不得,那只有等死而已,業緣境界同時都現前,業,就是我們身語意業;緣,我們過去造業都是緣取境界而有的,而現在那個業力,那個反作用力就出現了,所有的境界通通出現了,讓他非常痛苦。
「遂強作主宰,分付後事,」就開始吩咐後事了。
「高著蒲團,裝一鑪香,徐起坐定,默禱三寶龍天,悔過從前諸不善業;」他就高著蒲團,他就坐到蒲團上,裝一鑪香,默禱三寶龍天,就懺悔過去的不善業。
「若大限當盡,願承般若力,正念托生,早早出家;若得病愈,便棄俗為僧,早得悟明,廣度後學。」這個是他的願力,如果大限已盡,就要用這種般若的空慧的力量,正念托生,下輩子早早出家,如果病好,就棄俗為僧。
「作此願已,提箇無字,」這時候又用「無」這個話頭來修行,「回光自看,」回光,這個光不是物質的光,而是心的光,也就是心的覺照力,回光自看,看回自己,就是意識就放回到自己的身上,這個有一點像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,初於聞中,入流亡所,用這種迴光返照的方式,不管眼耳鼻舌身意生起了任何的色聲香味觸法,都不要理,你就往回看,往回觀,觀我聽到的聲音,並不是外面有聲音我才聽到,是我的耳根所生起,光是耳根也不知道外面的聲音,還有其他種種的緣,還必須靠我們的思維作用,我們的作意,我們的第六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等等,這些種種的緣,那叫作迴光返照。
「回光自看,未久之間,臟腑三四回動,只不管他,良久眼皮不動,又良久不見有身,只話頭不絕,至晚方起,病退一半,」這個就是打坐可以帶動我們內氣的流動,帶動內氣的流動,身體就有熱,有熱就可以去病,我們百病都是因寒而起的,它這邊提一個「無」字,就是把那個「無」來觀想它,觀想那個「無」,觀想那個「無」就必須要用力,如果沒有用力的話,「無」很容易就忘記,很容易就散失,這個就是看話頭的作用所在。
我們如果修一般的止觀,那在健康良好的時候可以,因為那時候我們的身體的情況還不錯,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所緣境上來觀這個所緣境的真相,慢慢由所緣境再回到內心。可是一到生病的時候,那個心力不足,就很難提起精神來關注所緣境。但是提起話頭更不容易,除非是平常有練習,同時那個心非常迫切,也就是要跟你拚了,死就死,有這種決心的時候才能夠把話頭提起。
這個話頭這裡是以「無」為話頭,以「無」這個話頭,對修行者來講是很有幫助,因為「無」提起來了就是提醒自己一切皆空,一切萬法本來面目皆是空,是我們的妄想才有種種善惡諸法出現,如果沒有妄想的話,一切萬法又回歸本來面目,一切皆空。
所以提起無也有這種幫助,除了說我們很用力,一用力的話,那個氣就提起來了。那同時也可以在智慧上提醒自己萬法皆空,他就提起這個「無」字,用這種「無」字的心光回看自己,不久以後,臟腑就動了三、四次,這個肚子就咕嚕咕嚕就三、四次動,那他還是提起「無」的話頭,還是不要放棄那個「無」的話頭,只不管他,「良久眼皮不動」,這個好久好久,那個眼皮又不動,因為那時候非常專注。又良久不見有身,這個身也不見了,「只是話頭不絕」,那個話頭沒有放下。「至晚方起」,到晚上他再起來,病已經退掉一半。
「復坐至三更四點,諸病盡退,」他又繼續坐,坐到凌晨三更四點,諸病就盡退了,那個病就好了,「身心輕安,」當然這些都是身體的小病,如果是大病用禪修還是治不了的,只是小病,可以用禪修來治療,這個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。他坐到凌晨,所有病也都退了,身心感到非常輕鬆。
我們看媒體的報導,泰國那些受困的能夠存活下來完全是那個教練當過十年和尚,教他們禪修,減少能量的消耗而已,現在已經救出十個人,還剩下三個人還沒有出來,那些是禪修的功能,不要動,不要動,那就是這樣子。
「身心輕安,八月至江陵落髮,一年起單行脚,」就到處去行腳,古時候的僧人都要行腳,行腳幹嘛?就是一方面增廣見聞,一方面去勘驗自己的心得,然後也可以請教各方的善知識。
「一年起單行脚,除中炊飯,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,不可斷續。」就是除掉在做飯的時候,否則那個念頭,話頭照樣提起。
「到黃龍歸堂,第一次睡魔來時,就座抖擻精神,輕輕敵退。」第一次睡魔來的時候就「就座」,還是坐在蒲團上,「抖擻精神」。我們有看過頭陀行這種修行,什麼叫作頭陀呢?頭陀,我們一般的解釋都是說是苦行,其實不是,頭陀不是苦行的意思,頭陀是梵文、巴利文的音譯,這個頭陀的意思就是抖擻,頭陀, dhūta,它就是抖擻精神,也就是提起精神,本來沒有力氣,靈魂跑掉了,那現在提起力氣,提起精神來,這個叫抖擻精神,這個叫作「頭陀行」。我們講說頭陀行,頭陀行有十二種或是十三種,從衣、食、住這三方面,有的時候包括藥,衣、食、住、藥三方面去抖擻精神,提起精神,那輕輕也就敵退了。
「第二次亦如是退。」第二次睡魔來了,又抖擻精神,讓自己精神ㄧ振,深呼吸一下,拉拉筋,伸展身體一下,這樣子睡魔也就退了。
「第三次睡魔重時,下地禮拜消遣,再上蒲團,規式已定,便趁此時打併睡魔。」可是來到第三次睡魔很重的時候,沒有辦法,抖擻精神還是沒有辦法,就「下地禮拜」,那就把這種疲倦給消遣掉,「再上蒲團」,就是睡魔重的時候就要下地禮拜,把那個睡的意識給打散掉,「規式已定」,也就是規矩就這麼定了,他自己定的規矩,如果在打坐的時候精神不好,他再抖擻一下,這個頭往上舉一下,深呼吸一下,身體脊椎骨往上頂一下,這樣子抖擻精神,第一次,然後第二次都是如此,如果第三次真的又有睡魔重的時候,他就下坐來懺悔禮拜,這個就是他的規定,「規式已定」,我規矩就自己這麼定。
「便趁此時打併睡魔」,也就是我定了這個規矩以後,就趁著這個時候,睡魔很重,再上蒲團還是用不上力的時候怎麼辦?那就只好去睡個覺,就「打併睡魔」,那就跟這個睡魔和解了,因為沒辦法,前後有三次,第一次,抖擻精神;第二次,抖擻精神;第三次,下坐禮拜懺悔,又回坐,又不行,又要打瞌睡,那我只好去休息。
那休息的時候,「初用枕短睡,後用臂,後不放倒身。」一開始的時候用這個枕頭,「短睡」也就是睡一點點時間,「後用臂」,那後來用這個胳臂,用這個手當枕頭,那這樣子也就是提醒自己不要睡成死豬,這樣子後用臂。「後不放倒身」,也就不再躺下來睡覺,我們稱為不倒單。
「過二三夜,日夜皆倦,」因為休息不夠,所以兩、三個晚上又是如此,白天、晚上都很疲倦。
「脚下浮逼逼地,忽然眼前如黑雲開,自身如新浴出一般清快。」過了兩、三天,「日夜皆倦」,而「腳下浮逼逼地」,浮逼逼地就是腳浮浮,人好像沒有靈魂般,浮浮,失魂一半,可是這個時候就是逼到盡頭,「忽然眼前如黑雲開」,忽然這個烏雲好像打開一般,自己好像如新浴出的清快,那個時候就是很清快的。
「心下疑團愈盛,不著用力,綿綿現前。」那個時候心下的疑團愈盛,那時候疑團越大,因為那時候越用功,那這個疑團就越來越大,到最後「不著用力,綿綿現前」,那時候就屬於不著用力,不再用力,自自然然疑團就綿綿現前,綿綿密密。
「一切聲色,五欲八風,皆入不得。」這個就是疑情成片,疑團很有力量,那個時候所有的色聲香味觸法,五欲八風完全進不了心,因為那個心裡面都被疑團包住,這個八風都吹不動。
「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,如秋空氣肅相似。」那種清淨的狀態有如銀盆盛雪,銀是已經是白色的,雪又是白色的,銀盆盛雪,「秋空氣肅」,秋天的天空一片烏雲也沒有,天高氣爽。
「卻思工夫雖好,無可決擇。」他就想到功夫不錯,那個心非常的清淨,可是沒有抉擇力,也就是那種智慧還沒有生起。
「起單入浙。」就到浙江去,
「在路辛苦,工夫退失。」又退了。
「至承天孤蟾和尚處歸堂,自誓未得悟明,斷不起單,月餘工夫復舊。」他就發誓如果沒有開悟,「斷不起單」,絕對不起坐,那個月餘的工夫,那個工夫又來了。
「其時遍身生瘡亦不顧,捨命趁逐工夫,自然得力,又做得病中工夫;」這個時候病中的工夫又有了,在前面有提到他下痢拉肚子,使不上力,可是後來他因為發起勇猛心,又提起話頭,慢慢練習,所以來到這個地方,「遍身生瘡」,就是全身都有瘡,可能就是衛生不好,因為沒有洗澡的關係,這個禪修是很精進的,是不得洗澡的,所以生瘡。「亦不顧,捨命趁逐工夫,自然得力」,那個時候病中的工夫比以前進步,病中也能用功。
「因赴齋出門,」赴齋出門,有人請齋飯就出門了,
「提話頭而行,」走路的時候又提起話頭,
「不覺行過齋家,又做得動中工夫。」這個時候又是動中的工夫,因為提起話頭,提起話頭了以後就不分辨環境,不曉得那個主人家在那裡,他沒有分辨力,因此就走過了這個齋家,這個表示動中也在定。
「到此卻似透水月華,急灘之上,亂波之中,觸不散,蕩不失,活鱍鱍地。」到這個時候就像透水月華,月華,透水月華,「月華」是水面上的蓮花,不被污泥所染,「急灘之上」,雖然這個灘頭浪很急,「亂波之中,觸不散,蕩不失」,也就是他這個疑團,也就是定的力量,三昧的力量都打散不掉,「活鱍鱍地」,這個是古字,這個古字應該比現在的字還來得生動,現在的字我們用三點水,三點水,發,而古字是魚加上發,那個魚還沒有死的時候,沒有水的時候,鱍鱍跳,那就活鱍鱍地。
「三月初六日,坐中正舉無字,」又把「無」字的話頭提起來,
「首座入堂燒香,打香盒作聲,忽然㘞地一聲,識得自己,捉敗趙州,」在那一天又舉起話頭,「首座」,首座就是一個寺廟裡面除了方丈、監院以外,就是首座,那就是等於是長老,資格最老,「首座入堂燒香,打香盒作聲」,打開香盒有這個聲音,「忽然㘞地一聲,那就㘞,這個字蠻有意思,是一個口,中間一個力量的力,這個力量的力並不是在口之外,這個力是在口裡面,就好像我們張開嘴巴用力地㘞,所以這個字叫作「㘞(ㄏㄜˋ)」,忽然㘞地一聲,忽然㘞,開悟了,他就㘞地一聲,認識了自己,怎麼認識?當然五陰無我,這個也就是破本參,這就破本參,證得空性,就入初歡喜地。
「識得自己,捉敗趙州」,為什麼捉敗趙州?因為趙州和尚回答僧人的問題,狗子有沒有佛性?趙州說沒有佛性,我現在捉敗,我就打敗了趙州和尚這句話,意思就是我知道趙州和尚這句話只是方便,只是為著令修行者產生疑情,如果趙州和尚回答說有,這個佛性一切眾生皆有,連無情也跟有情同圓種智,一切皆有佛性,對對對,經典就是這麼說的。
這樣子疑情就提不起來,因為大家都這麼說,那因此還有什麼好研究的。我們會研究一個問題是因為那個問題困擾我們很大,那個問題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樣,所以我們才會去研究問題,這個就是疑情。
疑情意思就是這個師父給了一個問題讓弟子去參究,去研究它,為什麼你這麼講?為什麼你這樣子無厘頭,這樣子不講道理?到這個時候,他開悟的時候,認識,識得自己以後,就捉敗趙州了,就曉得趙州和尚你講這句話,你胡說八道,因為你講這句話跟經典不合,我還是相信經上所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
所以趙州,我不相信你的話,你講沒有佛性,我不相信,這個時候又有了信心,以前相信佛說眾生皆有佛性,那被趙州一講,眾生,狗子沒有佛性,就開始起疑了,一整天都在研究這件事情,都在研究沒有佛性這件事情,好不容易把自己的疑團打破,打破了,我才知道趙州和尚胡說八道,還是佛說的對,這個時候我深信眾生皆有佛性。
這個禪師就是故意這樣子整人的,這個是好的老師,如果真的是根器,我們這個弟子如果是真的根器,這個老師就故意找碴,如果我們不是根器,這個老師一找碴,我們掉頭就走了,永遠疑情提不起來,那說我曉得你這個人不懂,你這個人大逆不道,你一點也不信佛,你還出家,這樣子掉頭就走,自己都開悟不了,因此是上根機者才會師父怎麼棒你,怎麼喝你都不會離開的,老是在那邊參究,在那邊研究,我就是要把這個疑問給參破,給了解,他就打敗了趙州。
「遂頌云:沒興路頭窮,踏翻波是水,超群老趙州,面目只如此。」「沒興路頭」,沒興路,沒興路就是沒有意味的話,也就是沒有道理,狗子沒有佛性,提起一個「無」,這個一點意思都沒有,「路窮」就是走到山窮水盡,走到路的盡頭,就是一直參究,一直參究「無」字,一直參究狗子沒有佛性這個話頭,參到最後,我終於發現真相。「踏翻波是水」,我即使踏翻了水桶,或是踏翻了海水,那個波還是水,波跟水沒有兩樣,這個水是波的所依,波只不過是水有了外力,因此有了波,就好像我們的佛性、真如心是不動的水,可是被攪動了以後就變成阿賴耶識,那個時候叫作「一念」,一念就生三細,境界就長六粗。
「超群老趙州,面目只如此」,它這個意思就是大家都說趙州和尚有多厲害,超群,超過其他的修行者,我看面目只如此,我看了他也不過如此,他怎麼說這狗子沒有佛性?這個太無明了,還虧他是一代的禪師,還虧他是超越眾人,我終於清了,那都假的,這個人虛有其表,他話都講錯了,他自己都不知道。
「秋間臨安見雪巖.退耕.石坑.虛舟.諸大老,」在秋天的時候,他就見了這幾位大老。
這個虛舟「勸往皖山。」又勸他去皖山。
「山問:光明寂照遍河沙,豈不是張拙秀才語?」「光明寂照」這象徵佛性,這個開悟了以後,把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,有如光明,光明雖然它不動,這個就是寂,可是它又能夠給予光明,又照,也就是動靜一如,一方面它是不動搖的,不生滅的,它是寂靜的,可是又有照明的功能,「光明寂照遍河沙,豈不是」,這個皖山長老就問這句話難道不是張拙秀才的話嗎?
「某開口,」他,蒙山異禪師他就想開口想要回答,是,想要回答,他才要開口。「山便喝出。」為什麼?因為這是禪師在勘驗他,勘驗他有沒有安住在佛性,有沒有真正的開悟,他故意就提出一個問題,光明寂照遍河沙,不就是張拙的詩嗎?那蒙山異禪師他想要開口,這個皖山就喝,喝出,這個就是臨濟宗的方法,棒喝。
「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。」這個時候開始行住坐臥、飲食都沒有意思,為什麼?因為這個心裡頭悶得很,我明明要說光明寂照遍河沙,我明明要回答,他卻不讓我回答,這個就是黃蓮有苦說不出,這苦的要命,可是啞巴又講不出來,那種悶,所以禁語,禪修最怕的就是禁語,禁語,我都不能講話,最重要的是現在不能滑手機,所以很痛苦…,這個行坐飲食都沒有意思,一點意思都沒有,因為嘴巴被封住了。
「經六箇月,次年春,因出城回,」出去城外又回來,
「上石梯子,忽然胸次疑礙氷釋,不知有身在路上行。」出城回來走這個石梯子,「忽然胸次」,次,什麼意思?就是中間,所以胸次就是胸腔中間,我這胸腔裡頭有疑礙,什麼叫作疑礙?就是有疑團,有障礙,一點意思都沒有,因為他想要把他開悟的境界說出來,可是那個皖山卻不讓他講,這個是不是最痛苦的事?我們明明,我的意見如何…,可是主席卻不讓我講,真的該殺,痛苦的要死,可是那個時候「忽然胸次疑礙冰釋」,整個身心空掉。
「不知有身在路上行。乃見山,」他又回去見這個皖山。
「山又問前語,」這個皖山又問光明寂照遍河沙,這個難道不是張拙秀才的詩嗎?他這麼一問。
「某便掀倒禪床,」這個時候他也不開口了,他就把這個「禪床」,床鋪整個給翻倒,就好像有人桌子翻倒,然後腳一踢,再也不管,這時候就是開悟。
「某便掀倒禪床,卻將從前數則極誵訛公案一一曉了。」那時候將從前有好幾則,「極誵訛」,誵訛就是錯誤很多,錯誤很多的公案,一一曉了。我們注意,這些疑情、公案、話頭通通是不講道理,如果講道理就提不起疑情,所以越不講道理越好,越不講道理越好,好像你去當兵,操你就是磨練,讓你吃苦就是磨練,那時候就完全了解了。
「諸仁者,參禪大須仔細,山僧若不得重慶一病,幾乎虛度,要緊在遇正知見人,所以古人朝參暮請,決擇身心,孜孜切切,究明此事。」這個是他後面的交代,「參禪大須仔細」,仔細就是那個細節都不可以放過,他在重慶一病,他還可以提起話頭,這個就表示他那個時候的工夫有了,他那個心不受身的影響,如果不得重慶一病,幾乎虛度,所以生病有時候是逆增上緣,會讓我們更加的精進。「要緊」,最重要的是要遇見正知見人,所以這個「古人朝參暮請」,朝參,早上參禪;暮請,晚上就是請示善知識來決擇,「決擇身心,孜孜切切,究明此事」。
「評曰:」,蓮池大師他這麼批評,
「他人因病而退惰,此老帶病而精修,終成大器。豈徒然哉!禪人病中,當以是痛自勉勵。」這個非常好,其他人因為病就退惰了,但是他卻能夠帶病精修,後來終成大器。
我們再看「楊州素菴田大士示眾」,「近來篤志參禪者少,纔參箇話頭,便被昏散二魔纏縛,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。信心重則疑情必重,疑情重則昏散自無。」好,這個近來發心要參禪的人非常少,纔參箇話頭就被昏散二種魔所纏縛了,昏就是昏沉,昏昏欲睡;散,就是散亂、掉舉,妄想紛飛,這是禪修的兩個毛病,而「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」,也就是說要提起疑情就能夠對治昏散,疑情提不起來就會昏沉,就會掉舉,如果「信心重則疑情必重」,我們昨天說明過了,對佛法三寶信心重,那麼疑情就是違反經論的話,違反常理的話,那疑情必重,這是一個原則,這很重要。也就是我們看禪宗公案這些禪師一定是講不合理的話,不講合理的話,目的就是要產生疑情,越不合理的話,疑情越能提起。
但是我們一般人都沒有思維的能力,趙州說狗子沒有佛性,一般人就喔!師父是大師,所以我真的相信狗沒有佛性,只有我才有佛性,你也沒有佛性,師父講什麼就聽什麼,那這種人不能參禪,要參禪一定要有思維的能力,尤其那些比較喜歡思辨的,越喜歡思辨的,越可以參禪,如果不喜歡思辨的,千萬不要參禪,因為你參不起來,這個疑情提不起來,因為師父說東,你就說東,師父說西,你就說西,因為這個趙州和尚,首先人家說他,問他狗子有沒有佛性,首先他說沒有,那後來又有人問他狗子有沒有佛性,有,那這個旁邊的小和尚就在那邊霧煞煞,到底有,還是沒有?參禪的人就不管。當趙州和尚說狗子沒有佛性,我就一直抓住這句話,我就提起疑情,我真的不相信你所說的話,你一代大師竟然也會這麼糊塗,我就要參破它。
等到他破了本參以後,就說不管趙州你講有佛性,沒有佛性,我通通不聽,為什麼不聽?因為你講的都胡說八道,其實他講的是對著根機,對著根機講有佛性,講沒有佛性,那我有自己的親身體驗,我曉得是怎麼回事,我曉得說有佛性,沒有佛性皆是方便,都只是方便,這個才是真如。
下一個,「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普說」,「二六時中,隨話頭而行,隨話頭而住,隨話頭而坐,隨話頭而臥。心如棘栗蓬相似,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吞噉,行住坐臥,通身是箇疑團,疑來疑去,終日獃樁樁地,聞聲睹色,管取㘞地一聲去在。」這個也是跟前面所講的,一天二十四小時,行住坐臥都是話頭,不要離開話頭這個所緣境,一直在參究,要參究,那這個越疑,那個力量越大,等到他破了以後,這個大疑大悟,那疑來疑去,所謂「疑來疑去」就是不管到哪裡都在參究疑情,都在想要了解這一句疑問句的真義是什麼,也就是要搞清楚,因為你講的話不合理,你講的話跟經論不一樣,我就要弄清楚。
所以「終日獃樁樁地」,一整天因為都在參究那個疑情,一整天都在想著那個疑情,想不是用第六識去找答案,而是那個疑情抓住就好,因為一有答案,很容易就又開始胡思亂想,所以那個疑情只是抓住,抓住為什麼趙州說狗子沒有佛性,一直抓住這個話頭,那終日呆樁樁地。
不管怎麼樣子,外境如何,到最後終有這個發明的時刻,一定會㘞,我終於知道了,那時候胸中的境界是講不出來的,因為只有我知道,你們都不知道,那時候就是禪宗的破本參,那破本參,我們說過了,也就是入歡喜地,也就是證得空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