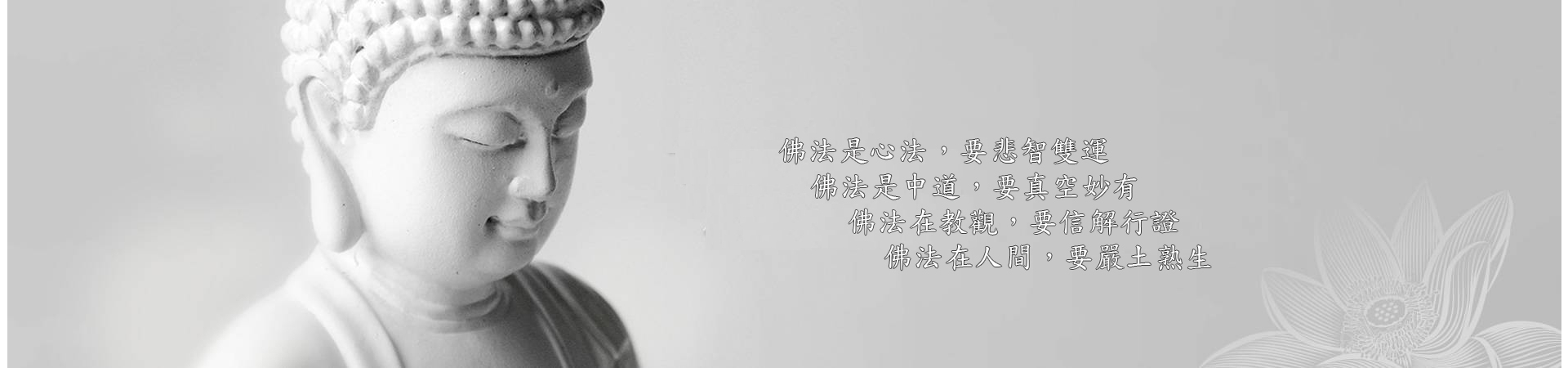老夢走了
鄭振煌
2009/10/08
[老夢癌症走了!]不久前我到南投上課,第一天就從報上看到這條新聞,只有短短幾行字。媒體對這位[今之陶淵明]的漠視,證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嚴重混淆,哲學家的死亡,其新聞性遠不如一位名模的寵物打噴嚏。2009/10/08
我有點遺憾,因為在他走的前一天課堂上,我對一位同學說:[明天我就要去南投上課,等我回台北後,我們一起去看老夢!]我不知道見了老夢要對他說什麼,他是無神論者,而我只略知佛法,我只能勸他萬緣放下,正念提起(甭說執持佛號一心不亂),他會聽嗎?應該會的,臨終者連一根草都會抓,我這麼相信。
可惜我判斷錯了!他竟然先走一歨。人生中有許多事稍縱即逝,因緣一錯過就後悔莫及了。
我和老夢並無深交,僅有數面之緣。
我們讀同一所大學,他讀的是哲學系,我讀的是外國語文學系,但我入校時他已經畢業了,我們並沒有見過面。那時台灣還處於戒嚴白色恐怖時期,沒有思想、學術、言論、結社、新聞等自由,文人把注意力轉向外國,大量翻譯外文書籍,類似魏晉南北朝的清談。老夢既專攻哲學,外文和華文底子又好,便成為翻譯界的聞人,年紀輕輕的就享譽島內外。我很欣賞他的文章,輕飄飄的,又富有出世的思想,很合我的胃口。
二、三十年後,我從報章得知,他厭煩了都市生活,自我放逐到花蓮海邊,過著沒有電、沒有自來水、沒有瓦斯、沒有電話、沒有任何現代文明的原始生活,整天望著太平洋放空腦袋。那段時間,我每隔二個星期就到花蓮講課,車子經過他的小屋子,就有衝動要下車見他,只是來去匆匆,總以為他會常住花蓮,機會多的是。
這樣子過了幾年,聽說他離開花蓮了,有關他的音訊全斷了。
大約十年前,我到陽明山訪友,這位朋友眉飛色舞地說要介紹朋友給我,原來就是老夢,應了那句古話:[踏破鐵鞋無覓處,得來全不費工夫。]
老夢向農家租了一間破屋子,生活用具簡單到不能再簡單,屋頂和牆壁處處可見漏洞,他竟然自得其樂。他帶領我們幾個人到附近的小學操場,席地而坐,喝起茶來。大家談得很高興,雖然他根本不接受佛法,我和他沒有共同的正經話題,但他有哲學家的豁達和文學家的優閒,妙語如珠,逗得我們開懷大笑。
我發現他拒絕了這個社會,對名利絲毫無動於心,最令我不解的是他似乎沒有生命動力,什麼都不想做,整天就是在山林中散步或與朋友泡茶聊天,一派閒雲野鶴的模樣。
後來幾次上陽明山,又見了他,我心中盤算如何從他學一些生命智慧,但他總是談些風花雪月,不談正經事。對於我的朋友既要學佛又要攻讀博士,他是完全不屑的。
他對於人間絕望了吧!我這麼想。我也有浪漫的思想,夢想以天為幕,以地為蓆,放縱此身於大塊之間;可是我沒有勇氣這麼做,一輩子勞勞碌碌,不知忙些什麼!
老夢雖然拒絕了社會,卻古道熱腸,心胸坦蕩。他和那群隱居在山中的靈性朋友互通有無,誰有什麼,其他人就有什麼,一聲吆喝,大家就到齊了,天南地北扯個沒完。
有一次我搭火車回南部老家探望母親,途中火車因會車暫停半個小時,我下車透透空氣,突然看見他走過來,原來他搭同一班車要回南部看他九十多高齡的父親,我才略知他的身世。鐵道旁有龍眼樹伸過枝枒來,龍眼成熟了,他隨手摘了一把吃了起來。我提醒他,這是別人家的,他笑了笑說,進了鐵路柵欄內就是乘客的。這是他的邏輯。
一年多前,醫生診斷出他的癌症已到末期,進進出出醫院,深受病磨,我沒有機會了解他如何調適心情。我不知道他看了《西藏生死書》之類的書籍否,或許他什麼都不需要,他已經解脫自在了,我的罣礙是多餘的。
年歲漸老,看盡生死相,比我年老的一個一個走了,與我同年紀的或甚至比我年輕的也走了不少,醫院和殯儀館變成經常去的地方,我也變得很雞婆,心急眾生該怎麼辦呢,一眼看過去,盡是剛強難化的眾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