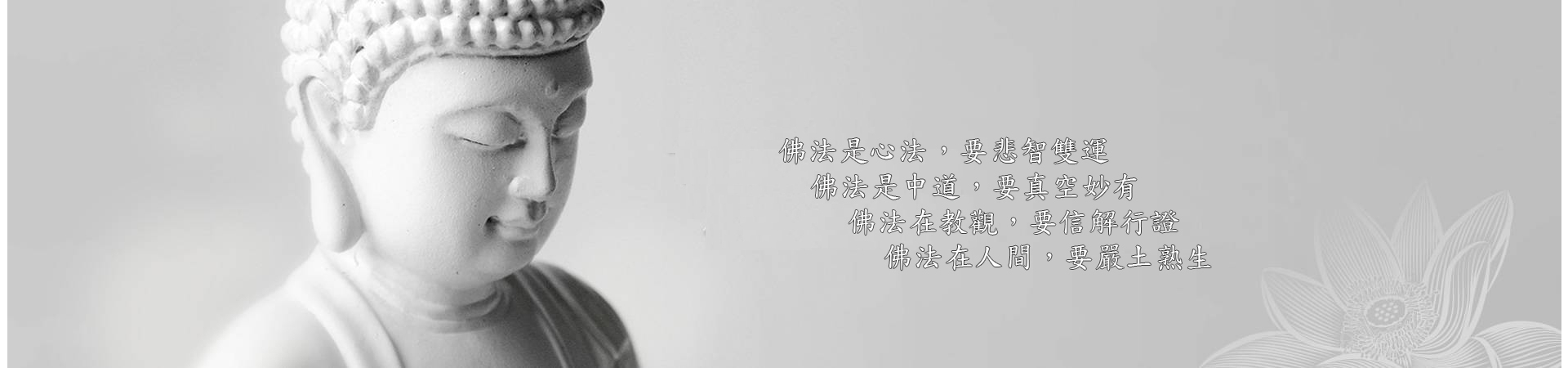誓為佛使
《佛使尊者–南傳佛教第一人》自序
《佛使尊者–南傳佛教第一人》自序
鄭振煌
2009/05/21
這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,而是一位學佛人的瞎子摸象記。雖然一輩子有點不務實際地浸淫於佛法,但對佛法還是一無所知,何況對一位不出世的佛門龍象!2009/05/21
我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,成長於東西方對峙冷戰、物質匱乏、資訊不通、思想封閉的年代。那時還沒有地球村、國際化的觀念。宗教是人類活動中最保守、最傳統的一環,在台灣我只接觸到漢傳佛教中最守舊、最遵古的淨土宗,念佛在那個年代是怪物的同義詞。
因為長期翻譯英文佛教資料為中文的關係,我有一扇小窗看到世界佛教。有一天,突然接到位於台北火車站前的佛光書局轉來的三本英文佛書,包裹內附了一張紙條,說明是一位陌生人留下指名要送我的。一直到現在,三十餘年過去了,我還不知道這位無名大德是誰,但卻大大改變了我此後的學佛方式。
這三本書原來是一位泰國比丘的開示紀錄,那時候的台灣對南傳佛教幾乎一無所知,而且鄙視為小乘。我瀏覽過這三本書,眼睛一亮,佛法竟然是這樣子!
我當時還是不知生死為何物的青年,雖然折服於漢傳佛教的博大精深,美則美矣,卻有無從下手之感。禪宗被認為是上根器者所修,坐禪有走火入魔的危險,不可以碰。密宗被武俠小說搞成陰陽怪氣,專以符咒害人。唸佛求生淨土,離死還很遠,西方極樂世界到底在哪裡,沒有人拿得出證據。六度四攝的菩薩道,豈是凡夫俗子做得來?這樣子渾渾噩噩的學佛了好多年,如霧裡看花,似有似無,不能說服自己學佛有什麼好處。
話說無名氏轉贈的三本書,第一本書談空性,以及如何在坐禪時、平時、臨終時安住空性,給我相當大的震撼。第二本書談禪修的方法,讓我恍然大悟,原來禪修應該是每一位學佛人的必修課,怎麼會被污名化呢?第三本書談佛教的基本觀念,算是入門書,我不禁嘖嘖稱奇,佛法竟然是如此貼近人生,完全不是談玄說妙的空談。
我陸續把這三本書翻譯成中文。第一本書名《菩提樹的心木》,作者是佛陀達沙(Buddhadasa最初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涵義),這可算是第一本介紹南傳佛教的中文書,至今仍廣泛流傳於華人世界。第二本書名《觀呼吸》,幾乎是修習入出念者的必讀指南。第三本書名《學佛釋疑》,專門回答初學佛人的問題。我又蒐集譯出《何來宗教》、《法味》等書。這些書籍引起華人世界對他的興趣,後來有更多的人投入翻譯,我也就封筆了。
因為這個不可思議的因緣,我開始認識南傳佛教,也前往南傳佛教地區參訪和學習禪修,在佛光山叢林學院開過[南傳佛教]的課,在佛教力行學院等處講過[清淨道論],發表過論文題為[佛使比丘與虛雲老和尚的禪法比較研究]。佛學學術界甚至把我歸類為南傳佛教學者,其實我什麼都沒學好,馬齒徒長,已然年過耳順,被人推向[老]字輩了。
我參訪過泰國五十次以上,對於泰國人民信佛之誠深為感動,佛教已經深入泰國文化的骨髓了,成為泰人生活最主要的元素。我常想世人如果都像泰人一樣信佛,世界就沒戰爭或暴力了。
有一年應邀前往泰國參加[法寶節]慶典,時間等於華人的元宵節,各處道場人山人海,以點蠟燭象徵佛法照亮吾人心燈。幾位朋友從曼谷搭機飛往泰南,再搭計程車前往聞名全球的一座森林寺院,探訪那位[南傳佛教第一人]。
那座寺院位於熱帶雨林中,沒有宏偉的佛堂,沒有電話,沒有電燈,只有一座圖書館和禪堂,二十來個大小不一的茅蓬錯落在森林中,彼此相距二三十公尺。知客師父帶領我們到一座小茅蓬,交給我們一把鎖匙,要我們離開時繳回就是了,既沒有盤問我們的身分,也沒有要我們登記姓名。這種完全的信任在當今社會已成絕響,禪修應該從這樣開始吧!
夜幕低垂,一輪明月從東方的原始森林中冉冉升起,大自然的交響樂正式上演,蟲鳴鳥叫,偶爾傳來幾聲狼嗥。半夜皓月當空,我一個人獨坐在長板凳上,身心俱融,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,再也沒有我、我所了。
第二天我走在晨星微曦中的森林小徑,突然聽到遠方山丘頂上傳來的唱誦聲,低沉而平穩,彷彿潺潺流水穿過茂密的竹林。循聲而至,豁然發現一群比丘在森林中做早課,原來五堂功課是可以在野地做的。
八點多鐘,大地醒過來了。我信步走到老和尚的臥室,果真是方丈室,房間只有一丈平方,簡陋的水泥屋,裡面放著幾塊石頭,石頭上擺著幾塊木板當床,蚊帳從天花板垂下。此外,什麼都沒有了,好一個頭陀行者!他對巴利三藏的通透理解,都以甚深禪定功夫來印證,成就了他一圖書館的開示錄音帶和書籍。
漸漸的,從四面八方湧進數十個人,老和尚坐在石椅上,比丘成八字形圍坐在他兩旁的沙地上,在家眾散坐在他前方的地上、石頭上或樹根上。老和尚針對信眾的問題侃侃而談,身旁有幾隻狗趴在地上做入定狀,有幾隻雞尋覓草間的食物。我聽不懂泰語,但我覺得回到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恆河流域,世尊就是在類似情境下說法的。
開示過後,我趨向老和尚跟前,內心澎湃著。他的潮州話已經走樣了,我聽不懂,他的英語也不怎麼靈光。那時,交談已經不重要了。有了心靈的交會,其他的都成了多餘的。他的侍者指著石頭上的方印,說上面刻著他的中文名字。我看不懂,特地照了相,回台灣後仔細推敲,才知道他的華文法號叫[佛使比丘]。
這是我和老和尚的唯一親身接觸,靈山勝會亙古常留。斯人已矣,我只能以這本小書緬懷一代大師。
二○○九年於中華維鬘學會